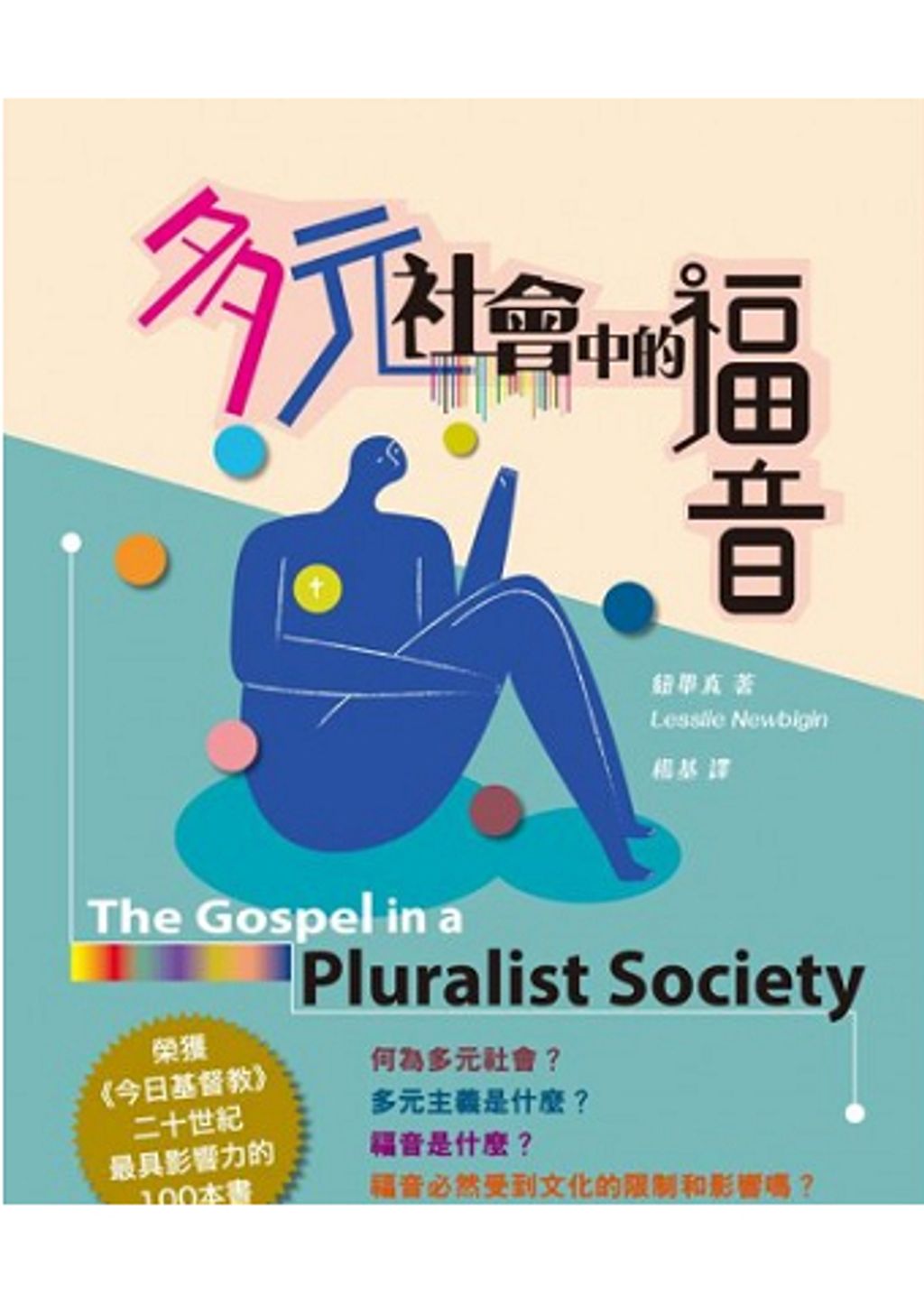
多元社會中的福音
英文名稱: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
作 者: 紐畢真
譯 者: 楊基
語 文: 繁體中文
版 次: 1
頁 數: 328
國際書號: 9789888250783
出版者: 宣道出版社 China Alliance Press
■內容簡介
福音與多元主義社會如何相干?在一個以宗教多元主義、種族多樣性和文化相對主義為特色的社會中,福音信息是什麼?基督徒面對現今的多元主義社會,應該致力於宣教還是對話?主流的輿論環境怎樣影響,甚或腐蝕,基督徒的信仰?
這本受人矚目的著作能夠解答這類問題。作者紐畢真對當代文化的分析精闢獨到,他指出基督徒能夠在這景況中自信地申明和維護信仰。本書反思深刻、發人深省、雅俗共賞,對這課題感興趣者、教會領袖及一般信徒讀後,必獲益良多。
■作者簡介
紐畢真
Lesslie Newbigin
(1909-1998)
紐畢真牧師生於英國泰恩河畔紐卡素。他在劍橋大學學士畢業後,於蘇格蘭格拉斯哥基督徒學生運動任職祕書。之後,他在劍橋大學西敏寺學院研讀神學,並在1936年為蘇格蘭教會愛丁堡區會所按立。同年紐畢真與海倫.亨德森結婚。婚後他以蘇格蘭教會宣教士身分,與妻子一同前往印度宣教。
在1947年紐畢真獲委任為南印度教會主教。他也曾擔任國際宣教協會祕書長、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副祕書長和該協會的世界宣教及福音事工部門首任主任等。
在1965年他重返印度擔任馬德拉斯主教,在任直至1974年退休。之後,他居於英格蘭倫敦,直至逝世。他著作甚豐,中譯本包括《聖經走一回》、《上帝家裏的人》、《應世的宗教》。
■前言
雖然教會一直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中見證基督,但是,就如何看待這種社會環境,近年出現了一些新的認識,多元主義(pluralism)正在迅速呈現意識形態的某些特徵。因此,我們亟待重新理解基督教會在今天多元化的世界中宣教的性質和作用。
當今世界,各種文化和宗教紛繁複雜,普世教會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內部正在探索如何在這種環境中忠實地傳達福音並且忠實地執行教會的宣教使命。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的著作為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紐畢真發現,在當今許多的討論中都有相對主義(relativism)的鬼影,這種思想十分危險。他不接受將「事實的世界」(world of facts)與「價值的世界」(world of values)二分的觀點。當代基督徒,尤其是西方的基督徒受制於這種二分觀念,在文化面前表現出種種懦弱或焦慮,紐畢真為之惋惜。《多元社會中的福音》是一個劃時代的呼召,它呼喚基督徒重新相信耶穌基督的福音。這本書讓我們看到「身為基督徒,我們如何在今天所處的這種智性環境中更堅定地捍衛信仰」。
雖然看似螳臂當車,但紐畢真敢於特立獨行,堅持自己的立場,並為自己的信念辯護。他的話清晰明白,令人振奮,這源於他多年牧會的經驗、對宣教的委身、普世教會的異象以及對福音毫不動搖的信心。
關於多元環境中基督教信仰的地位和教會使命,這方面的書籍汗牛充棟。但許多書籍是寫給學者看的。而紐畢真的讀者則廣泛得多。基督徒應該如何用實際的方法回應多元主義處境所提出的問題?就此,紐畢真多次提出多項建議。這些建議的基礎是紐畢真對聖經見證和基督教傳統的具體理解,但是紐畢真的論證水準讓多數書籍甘拜下風。多虧紐畢真,我們看到一種新的可能性:讓教會會眾參與討論多元主義,讓他們參與不同信仰之間的對話,通常這種討論不會發生在會眾這個層面。
在前幾章,紐畢真分析了當前基督教信心危機的若干根源。這幾章的理論和認識論架構深受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影響,明顯以西方狀況為導向,容易引發爭議。然而,這些內容以嶄新的方式提出了一些問題,並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參照系,人們可以在這個參照系的框架內提出並富有成效地探討關鍵的宣教學問題。
紐畢真把認識論的看法及其神學表達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不一定所有讀者都喜歡。讀者或許會感到福音的透視特徵和故事特徵與福音的絕對主張之間存在某種張力。但是,這也是一個富有創意的張力。紐畢真提出,「基督教的故事給我們提供了一副不同的鏡片,我們不是去看這副鏡片,而是透過這副鏡片去看世界。」沿著這個思路,「我們可以克服教會內部自由派和基要派之間的劇烈衝突」。他還指出基督教故事與其它故事之間須要「展開對話」,也能展開對話。紐畢真強調,如果基督教故事要和其他故事展開有效對話,那麼基督徒必須積極健康地面對基督教傳統,在思想和實踐兩方面,懷著信心和獻身精神,進入傳統。
紐畢真關於教會宣教使命的論述,鞏固並強化了普世教會關於宣教工作和福音工作的許多主張。例如:會眾在宣教事工中具有核心作用;教會亟待培訓一些牧師,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幫助基層平信徒參加宣教工作。這兩個問題都在本書中得到了強有力的論述。紐畢真說會眾是「福音的詮釋者」(the hermeneutic of the gospel),他們是屬上帝的百姓,組成一個全新的共同體;紐畢真進一步強調了這個共同體的本質及目的。今天,許多教會都在想方設法培養宣教的會眾,本書的積極建議極有裨益。
福音在一個多元主義的社會中有何地位和作用?這個問題不可迴避,討論也必將持續下去。紐畢真的寶貴貢獻會激發那些重視多元環境的人以同樣嚴肅認真的態度看待某些與多元社會相關的基本神學問題。本書還將挑戰那些曲意迎合各種各樣相對主義的人。紐畢真呼籲基督徒要心意更新,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持對福音的信心。對教會的生命和普世教會合一工作而言,這種信心是不可或缺的。
基斯杜化.杜萊辛
(Christopher Duraisingh)
世界基督教協進會世界宣教和福音事工委員會主任
(Director, WCC Commission on World Missions and Evangelism)
■作者序
這本書基本上是1988年度我在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擔任亞歷山大.羅伯森(Alexander Robertson)講師期間使用的系列講稿。我很感激神學院的喬治.紐蘭茲(George Newlands)教授和他的同事,感謝他們邀請我前來講學;也感謝他們在我暫居格拉斯哥期間款待我和內人。我也很感謝我的學生,他們積極參與小組討論,激發了我的思想。
我不認為自己的思想獨一無二,也不覺得自己是學者。我是牧者和傳道人,只想與其他牧者同行及與眾人分享我一些浮光掠影的想法,這些想法來自我閱讀相關主題的書籍,而這些閱讀非常不系統。學術著作會列明所有引用資料,聲明作者已經提到一切相關文獻。我若使用注腳以提高本書的身價,就有冒充學術著作之嫌,而我實無此意。所以,最好在序言部分直接承認我受惠於許多作者,就不用每次引用都致謝。整本書,特別是前五章大量依據邁克爾.波蘭尼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1958年)一書。本書多處受惠於阿拉斯泰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尤其是他的著作《誰的正義?哪種理性?》(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1988年)。第九章很多思想來自亨德里克斯.伯克富(Hendrikus Berkhof)所著《基督,歷史的意義》(Christ, the Meaning of History,1966年)一書。第十六章採用了華特.溫克(Walter Wink)所著《命名權勢》(Naming the Powers,1984年)和《揭開掌權者的面具》(Unmasking the Powers,1986年)兩本書上的一些思想。
我和所有說英語的人一樣,用陽性代名詞指全人類,包括男女。出於正當的原因,許多讀者現在已經不能接受這種用法。這就為難了作者。如果每個地方都要用兩個人稱代詞(「他或她」),那句子就不忍卒讀了。因此我既用「他」也使用「她」來泛指二者,並希望不至於厚此薄彼。我希望人們不要因此指控我有什麼道德不當。
我非常感激塞利奧克(Selly Oak)校區的丹.畢比(Dan Beeby)博士和哈樂德.特納(Harold Turner)博士,他們閱讀了我的初稿,並提出寶貴意見。本書成品若有缺陷,與他們無關。
紐畢真
於伯明翰(Birmingham)塞利奧克
■目錄
前言
作者序
導言
第一章 多元主義文化中的教條和懷疑
第二章 多元主義的若干根源
第三章 知與信
第四章 權威、自治和傳統
第五章 理性、啟示和體驗
第六章 歷史中的啟示
第七章 揀選的邏輯
第八章 聖經,作為普世史
第九章 基督,歷史的線索
第十章 宣教的邏輯
第十一章 宣教使命:話語、行為和新生命
第十二章 處境化:真與假
第十三章 別無他名
第十四章 福音與各種宗教
第十五章 福音與各種文化
第十六章 執政掌權者與人民
第十七章 世俗社會的迷思
第十八章 會眾是福音的詮釋者
第十九章 牧師帶領會眾宣教
第二十章 相信福音
人名對照表
■內文試讀
人們常說我們生活在多元主義的社會。所謂多元主義,不僅是說社會具有多種文化、多種宗教和多種生活方式,而是說這種多元性本身受到普遍認可和推崇。西方世界所謂的多元社會是與早期基督教世界的情形相比,當時社會有一套由基督教界定的、社會普遍接受的教義,用來規範社會成員的一切信仰和行為。與之相反,今天人們認為多元主義是世俗社會的本質特徵,這種社會沒有官方的信仰模式或行為模式。因此,人們認為這種社會是自由的社會,不受任何教條的約束,反而具有一種批判一切的精神,準備隨時批判(甚至懷疑)任何教條。我做這些研究,就是為了反思當代這些認識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確的,又包含哪些迷思的要素(elements of myth)。因為長期確立的教條肯定不容批判,除非這種批判基於某種別的信仰。批判不可能出於空白的頭腦。
人們常說(或暗示)現代科學的興起顛覆了基督教世界觀在西方歐美社會的統治地位,但是這種說法顯然過於簡單。格拉夫.雷文特洛(Graf Reventlow)在他的巨著《聖經的權威及現代世界的崛起》(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World)中表明,人文主義(humanist)傳統很早就開始攻擊基督教,而我們從西方文化的古典希臘和羅馬要素中繼承了這種傳統。這一傳統於文藝復興時期浮出水面,勢頭強勁,並在宗教改革發揮了部分作用。人文主義傳統本身由許多要素構成。這些要素可以分為兩個支流。一支是理性主義(rationalist)傳統,主要來源於古希臘和斯多葛主義思想,這種思想斷言人類理性是認識真理的唯一工具。另一支則是靈性主義(spiritualist)傳統,它主要吸收了歐洲和印度所共有的古老思想,這種思想斷言人的靈能夠通過奧祕體驗直接與終極真理和生命源頭進行交流。這兩類傳統看似相反,卻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它們都堅信一點(都有一個未經質疑的假設):歷史事件非終極真理之源。真理必須是一切有理性的人都能領會的東西,真理必須脫離一切歷史偶然性,任何理性的人只要運用理性思考或與神性(the divine)心靈相交都能得到真理。這一思想最著名的表達莫過於萊辛的名言:歷史的偶然真理永遠不能確立普遍的理性真理。對人文主義傳統而言,這一說法儼然就是公理,過去不容置疑,現在亦然。
格拉夫.雷文特洛的研究表明,在17世紀的後半葉及整個18世紀,雖然普通基督徒還生活在聖經的世界中,但知識分子日益受制於人文主義傳統。所以,連那些竭力捍衛基督教信仰的人,他們的辯護不過就是:基督教信仰「合乎理性」,也就是說基督教信仰與人文主義的基本假設並不矛盾。回顧歷史,就可以看到這種辯護可說是節節敗退。比如:人們一度認為,上帝為我們提供了兩個途徑讓我們認識祂:有一本書稱為聖經,還有一本書就是自然。我們首先運用理性從自然來認識真理,凡是我們不能運用理性從自然之書讀到的真理,上帝就用聖經告訴我們。這樣,聖經就成了自然之書的補充。按照這種觀點,我們不是聖經故事的一部分,在上帝導演的這場講述「創造、墮落、救贖和最終成就」的大戲之中,我們自己並非演員。我們生活在一個超越時間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真理與時間無關,它適用於歷世歷代的萬族萬民,並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與人相交。18世紀延續了這種趨勢,我們發現那些要緊的真理都來自於自然之書、來自於理性和良知;而聖經的道理成了無關緊要的瑣事,用不著爭辯。但是,我們最後竟然到達無路可退的境地:聖經必須接受人的理性和良知的審查,並且人的理性和良知發現聖經前後矛盾、荒唐可笑,盡是些誇張的故事,甚至明顯不道德。
為了回應這些攻擊,基督教世界寫出了各種護教著作。這些作品,尤其是18世紀的作品,最令人痛心之處是它們竟然在很大程度上默認攻擊者的種種假設。他們的辯護只是「基督教合乎理性」。基督教可以吻合一切理性的人所堅持的各種假設。可是很少有人敢說這些假設本身應當受到質疑。這種辯護的方法實際上是一種戰術撤退,但戰術撤退要是太多,就會潰不成軍。有史為證。
或許我可以用一位外國宣教士的經歷來說明我的意思。我年輕的時候當過宣教士,每周要在我所住的鎮裡的拉馬克里斯納傳道會(Ramakrishna Mission)寺院呆一晚上。我和那兒的僧侶一起坐在地上學習《奧義書》(Upanishads)和福音書。寺院宏偉的大廳和拉馬克里斯納傳道會所有建築一樣,陳列著許多偉大宗教導師的畫像。當然,其中也包括耶穌的畫像。每年聖誕,他們都在耶穌的畫像前拜祂。雖然他們拜耶穌,但認為耶穌不過是上帝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眾多化身的其中一位而已。我身為外國宣教士,當然不認為這是印度人改信基督教的一個步驟。這是印度教的世界觀同化(co-opt)了耶穌。因果報應(karma)和輪回(samsara)永無休止的循環把耶穌也困於其中,和我們一樣。印度人馴服了耶穌,把祂融入印度教的世界觀。而這個世界觀本身卻地位穩固。我經過許多事情之後,才逐漸發現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也有這種馴服現象,我也想追求一種「合理的基督教」,可以用20世紀英國人知識結構的術語加以辯護,而非讓基督教用一種全新的亮光來批判我的一切知識結構。說到「馴服」福音,我也難辭其咎。
印度當時是宗教多元的社會,現在也是。雖然印度社會體系的結構相當僵化,但人們能自由地選擇宗教道路。二戰後,歐洲社會也逐漸走向印度這種宗教多元主義。當年,我坐在地上和印度教朋友討論宗教的時候,英國名義上還是基督教國家。除了小型猶太社區之外,英國沒有明顯的非基督徒社區。傳揚福音就是呼籲英國人回歸他們靈性的根源。傳福音和復興運動之間沒有什麼差別。今天的情形則不同。我們的大城市有大量印度教信徒、錫克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的社區。他們的英國鄰居很快就會發現,這些外來者常常比本地的普通基督徒更加聖潔、更加熱衷參加宗教活動、更加虔誠。在這樣的社會中,「傳福音」到底是什麼意思?當然不是我們過去所理解的「回歸宗教」。這些宗教徒不須要回歸宗教;他們本來就是非常虔誠的宗教徒。既然他們早就有值得尊重的宗教,那將我們的宗教強加在他們身上,豈不是傲慢之舉?人們自然會提出這類問題。從這些問題出發,我們很快就進入一種尷尬的處境。英國聯合歸正教會(United Reformed Church)近期會議上一位與會者提到這種現象:針對那些不信耶穌的英國人時,我們就談「傳福音」;針對那些來自亞洲和西印度的鄰舍時,我們就談「信仰對話」。福音就像南非公園裡的福利設施,只供白人享用。來自亞洲的基督徒認為這種狀況簡直匪夷所思。
當然我這裡所談的是非常深奧的問題,涉及基督徒應當如何認識世界的一些主要宗教,這個問題後面還要展開論述。但是在多宗教的環境中,基督徒不願意使用傳福音的語言,這暴露了當代文化的一個頑症。前面講過,早在16和17世紀,在我們文化裡,聖經的元素與人文主義的元素之間,以及聖經所塑造的世界觀與理性人文主義和靈性人文主義所塑造的世界觀之間就已經發生衝突。當時,這兩種對立的元素之間雖然存在張力,但仍從屬於同一種共識。人們教導聖經,用教理問答來總結聖經教導,公認這些為真理。當時那些劃時代的偉大思想家無一不是基督徒,他們堅信神學和物理學、數學一樣,都是無縫的真理之袍上的經絲緯線。艾薩克.牛頓(Issac Newton)的聰明才智很多用於研究神學,在他看來,神學與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並非隔行如隔山。然而,我們今天知道,基督教世界觀與人文主義之間當時就存在張力,而人文主義傳統最終佔了上風。聖經節節敗退,不得不為愈來愈多的內容辯護,接受理性和良知的嚴厲審判。一旦聖經看似難以自圓其說,張力就會變成隔閡。聖經變成了一本玄書,它只能詮釋靈魂生命、內在生命以及屬靈生命——至少在那些樂意受聖經影響的人看來聖經就是如此。公共領域沒有聖經的容身之所。科學家和哲學家不再是神學家和聖經學者。教理問答手冊不再納入公立學校課程。學校裡可能開設所謂「宗教研究」的課程,因為宗教是人類生活的事實。但是宗教徒所信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並不是事實。只有經得起現代科學方法批判審查的,才是事實和公共真理;別的都是教條(dogma)。你自己要信沒問題,但你說它是事實,那就是傲慢。這樣一來,基督徒如何正確傳揚福音?如何把福音當做真理來傳播?如何才能避免現代思想的假設馴服福音,而是用福音挑戰現代思想的假設並修正這些假設?這就是這幾章關心的問題。
或許我們可以先來討論我剛用的詞「教條(dogma)」。因為,眾所周知,英語中由此衍生的形容詞——「教條的(dogmatic)」——在我們的語言中正好代表一切無知和傲慢,而不表示「追求真理」。
「教條(Dogma)」一詞源於dokein,意思是「顯然」。這個詞是指公認為好的並因此得以傳播的東西。使徒行傳十六章四節耶路撒冷公會的規條用的就是這個詞。在教會歷史上,這個詞多用來指權威所頒布的並須要用信心接受的東西。這個用法,歐洲人用了上千年。而在當代,情況正好反過來,隨時質疑教條(dogma)被視為是學術上成熟和有能力的表現。
毫無疑問,基督教始於宣揚某一權威所賜下的資訊。這是事實,不管我們怎麼看。保羅說自己不是新的神學教師,而是一位使者,是有權柄的主所親自委任的,他的任務是宣揚一個新的事實:上帝已經採取了決定性的行動,通過耶穌的工作、死亡和復活,上帝啟示並成就了祂拯救全世界的旨意。顯然,新約就此事實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但是新約所說的一切總是圍繞這個事實。我年邁的老師卡耐基.辛普森(Carnegie Simpson)稱之為「基督的事實」(the fact of Christ)。並且,無論新約作者之間有何差異,他們就這個事實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認為這個事實對全世界所有人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這一宣告需要人用信心來回應。這個真理不是世俗之事,不能用人類的普遍經驗證明。相反,人接受這一宣告以後,才能通過它來正確認識人類的一切經驗。這一宣告是光源,藉著這光,才能看到事物的本相;沒有這光,就不能真正認識事物的本相。這一宣告只依據資訊自身的權威,而不依據別的權威。如果有人質疑宣告者,要他們說明權柄從何而來,他們只說「奉耶穌的名」。他們說得很有膽量,認為這就是唯一的真理,而不是諸多觀點中的一種。當然,別人可以拒絕。事實上,他們確實拒絕了。新約反覆強調,使徒的信息與世界的智慧根本就是矛盾的。我們在約翰的記錄中看到耶穌如何與本民族的各種權威激辯,這是上述矛盾的高潮。但是,這種矛盾最開始就暗潮洶湧,耶穌傳道工作一開始(根據馬可福音),就要求人必須悔改、徹底轉變、「心意」更新,走一條與世俗截然相反的道路,這樣才能認識那個新的現實(new reality)——上帝就在這裡,現在就是上帝掌權的時候。
教會可能在歷史上扭曲和誤用了教條(dogma)的概念,事實上這個詞確實遭到了嚴重扭曲和誤用。然而,這個詞所指代的現實(reality)一開始就存在,而且是福音的固有內容。有一個全新的東西已賜給我們,是不容置疑的。我們對眾人皆有的普遍經驗進行理性思考,得不出這個東西。這是一個新的事實,是恩典的禮物,要以信心領受。而且,它聲稱自己就是那唯一的真理,而不僅是一種可能成立的觀點。它就是那石頭,若不作為一切知行的基石,便是叫人跌入災禍的絆腳石。那些受託之人——他們受託不是因為他們自己聰明、智慧或聖潔——不能依據別的任何所謂可靠之事證明這是真理:他們只能順服它,隨行隨講。這就是教條,是上帝所賜的東西,要我們用信心加以贊同。
當然,正是這點,我們文化中的另一股力量——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要素——要起來反對。將每個真理主張置於理性的批判審查之下,這是人成熟的特徵——我們今天的文化如此,保羅當年的希臘世界亦然。我們的文化願意並且能夠在理性和經驗的光照下,無所畏懼地嚴厲批判一切教條;我們可能比任何古代文化更喜歡吹噓自己的這種反思能力。因此,宣教士和傳福音的人自然成了眾人懷疑的對象,因為他竟敢斷言真理必須以信心接受。他不就是個食古不化的前朝餘孽?真理豈不比任何宗教傳統或文化傳統更宏大、更豐富、更複雜?豈不是每個人都必須接受這點?我們豈不應該懷著謙卑求真的態度,保持思想開放,隨時聆聽人類各種宗教體驗的說法?停止佈道,參與對話,聆聽別人的體驗,分享我們的體驗,不要取代別人的宗教體驗,而是要通過分享我們的宗教經驗來豐富他們,也豐富我們——這樣豈不是更加誠實,更加謙卑?只有開放的思想才能指望找到真理,而教條是開放思想之敵。
人們可能說這種觀點(基督教的觀點)顯然只適用於某些類型的真理。但這種結論過於匆忙,流於膚淺。儘管許多教育家積極鼓勵學生要保持思想開放,自己決定什麼是真理,但是在課堂上問學生巴黎是法國還是比利時首都的老師不會喜歡學生說自己對此持開放態度。我們的文化並不完全接受多元主義的原則。我們在所謂「價值」的世界與「事實」的世界之間劃了一道鴻溝,這是我們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也是我們須要深入思考的特徵。在價值的世界,我們是多元主義者;價值是個人選擇的問題。在事實的世界,我們不是多元主義者;事實就是事實,不管你喜不喜歡。可見,在這個文化中,教會及教會的佈道屬於「價值」的世界。教會是一種「高尚的事業」,要靠好人支持。倘若沒人支持,教會就會崩潰。人們都認為教會不關乎事實(fact),不關乎最終掌權的現實(realities),不關乎那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最後都要承認的現實。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基督徒滿懷信心地宣告自己的信仰,聽起來好像是某些人傲慢地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只要教會不要太過分,只要他們謙卑地提出自己的信仰,只要他們認為自己的信仰不過是意識形態超市裡琳琅滿目的商品之一,那就不會惹禍。但是,斷言福音所啟示的真理應當控制公眾生活,那就是冒犯眾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