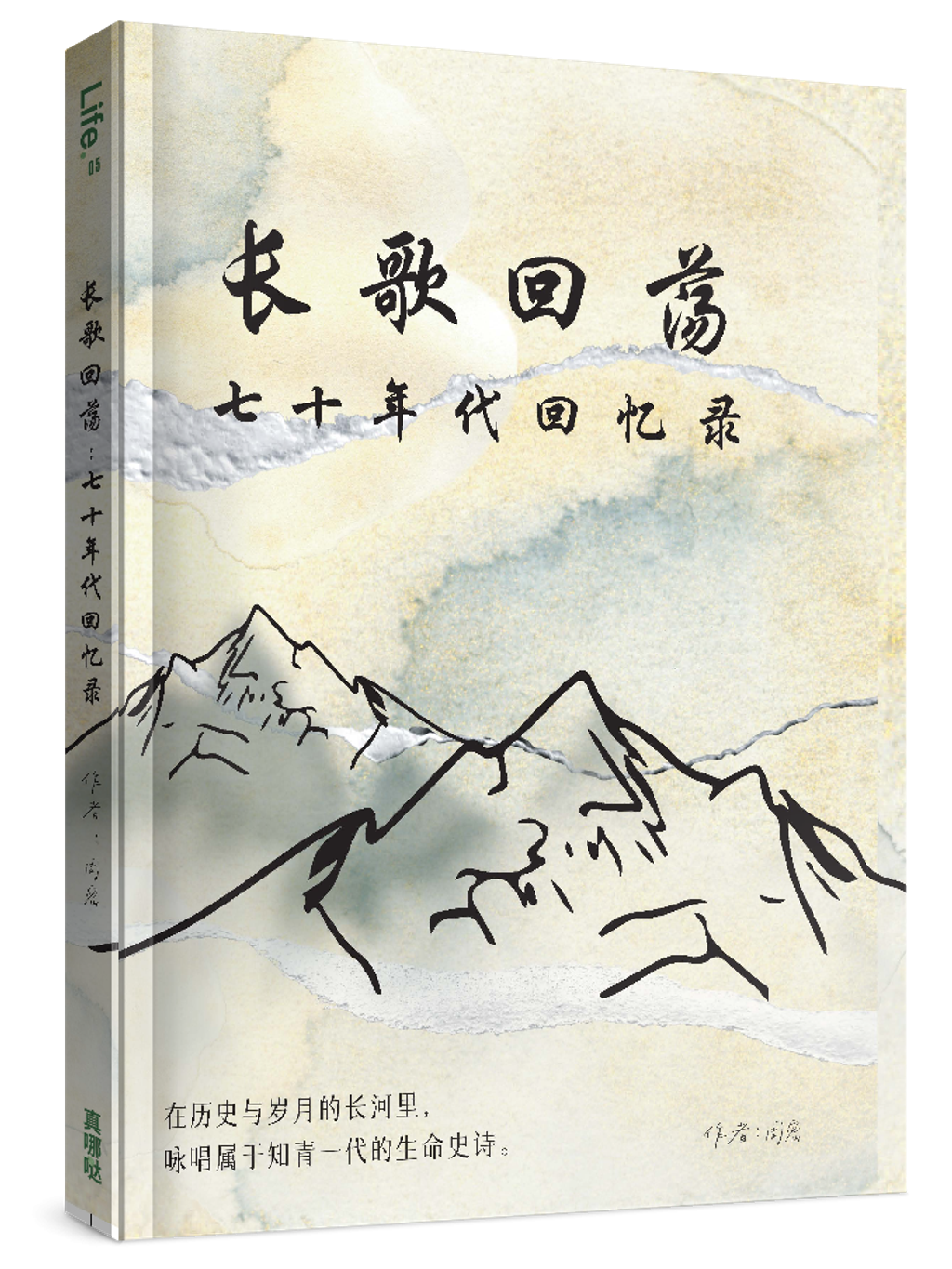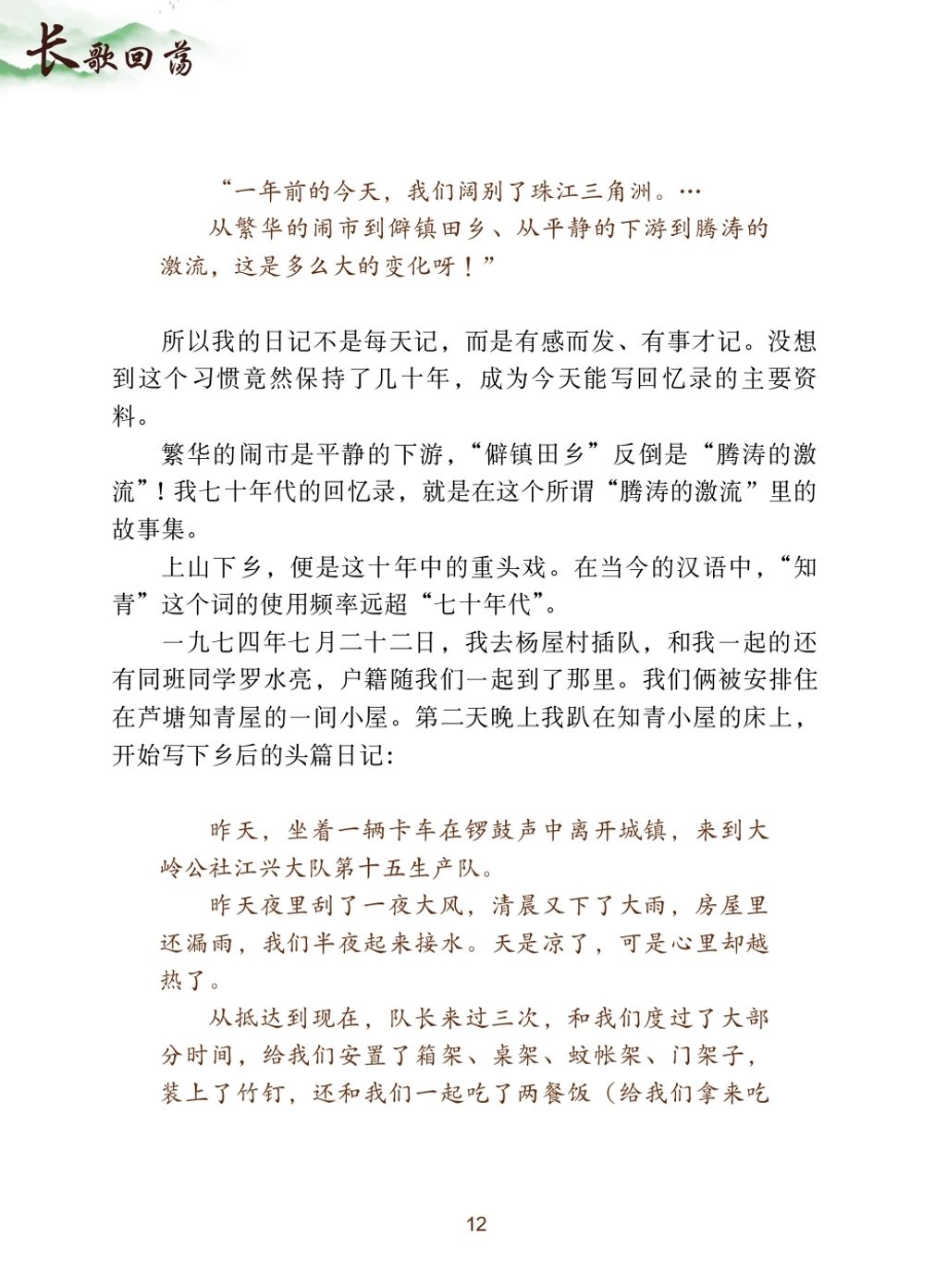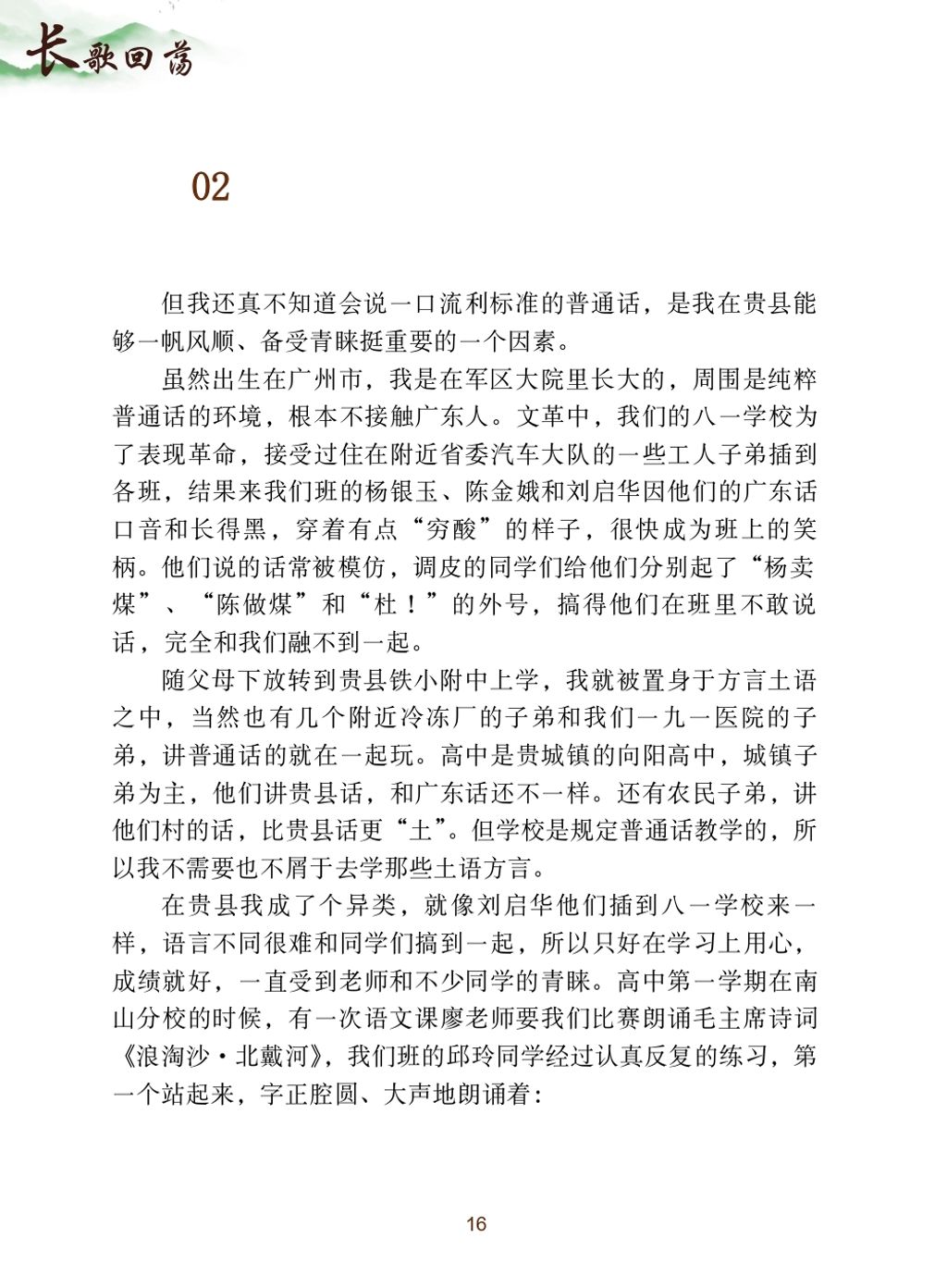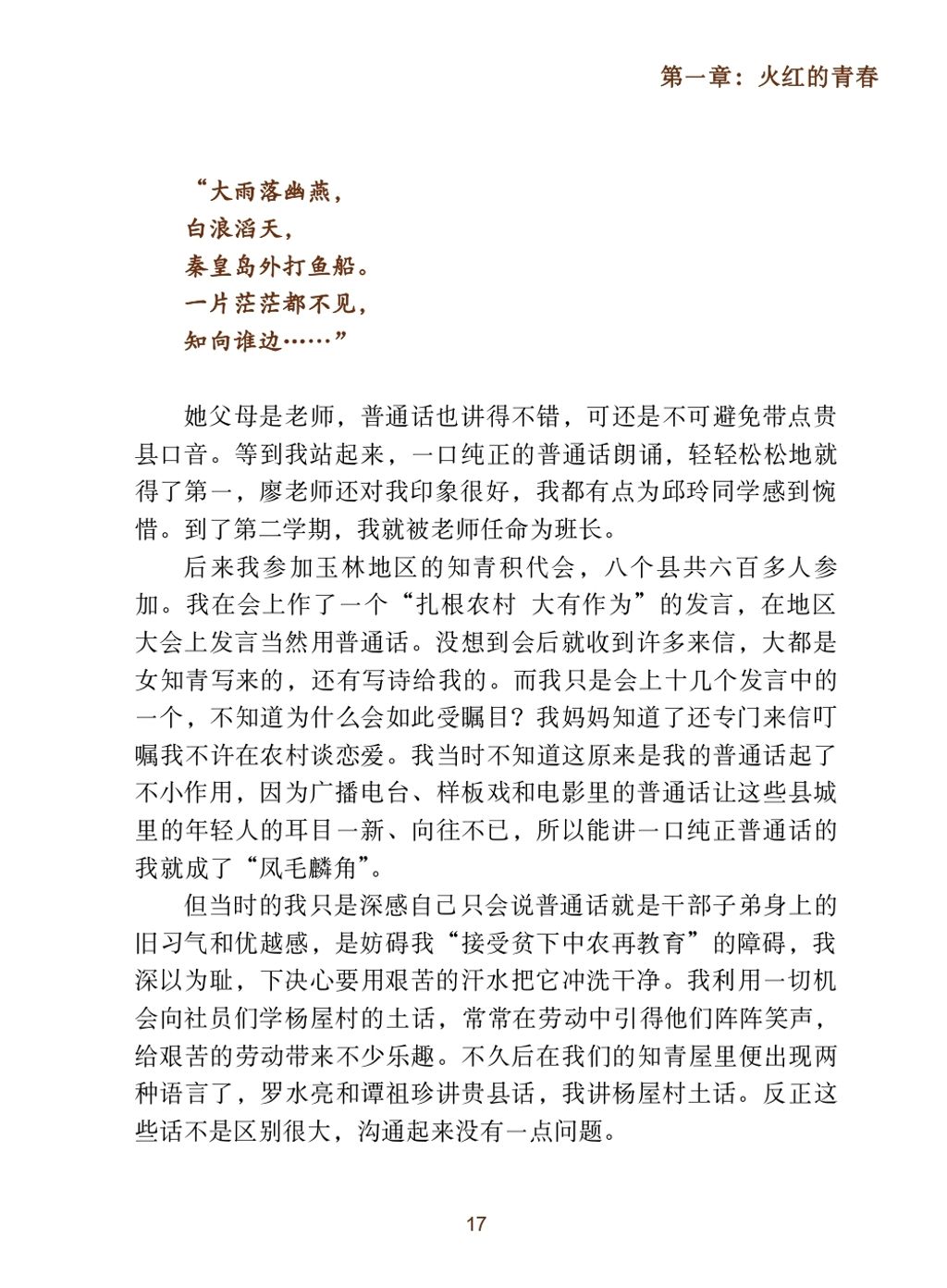长歌回荡:七十年代回忆录(簡)
出 版 商 真哪哒出版社
系列名称 Life 5
作 者 周密
ISBN 978-626-7599-50-1
CIP 782.886
EAN 9786267599501
出版日期 2025-11
语文别 简体中文
页数开本 尺寸:170*230mm
页数:320页
印刷装订 黑白胶装
类别 个人成长 历史回顾 回忆录
■本书简介
记载了动荡的七十年代成长的经历,展现了在革命浪潮下,
年轻人如何被推向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从海边的歌声到革命的口号,本书生动地再现了七十年代的社会氛围。透过丰富的回忆,读者将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青春活力与理想主义,幷思考在巨变中,人们如何寻找自己的定位与信仰。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幷反思了过去的经历对当今生活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部关于勇气、坚持与希望的作品,鼓舞着每一位读者去面对自己的挑战,幷寻找生命中的意义。
这本书适合所有对历史、社会变迁和个人成长故事感兴趣的读者。无论你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还是对过去充满好奇的年轻一代,这本书都将带给你深刻的思考与感动。
■前言
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二日,我到哈佛商学院参加毕业三十五周年庆典,副院长 Fritz Foley 教授约我去他办公室会面。没想到一个多小时的见面从头到尾都是要我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这让我知道原来故事是不该隐藏的,应该说出来,大家其实都是有兴趣的。
我的故事要回到七十年代、从上山下乡说起 …
大海边哎
沙滩上哎
风卷榕树沙沙响
渔家姑娘在海边
织呀嘛织渔网
织呀嘛织渔网
……
这是江兴三塘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排练,杨屋村五叔的女儿杨玉兰,用她清亮高亢的声音唱着这首〈渔家姑娘在海边〉。歌声穿越隆冬的夜空,在江兴的村落中散开;歌声穿越过了几十年,仍回荡在我的心间。
七十年代是我成长的年代。启蒙阶段就被过早地推入了一个风雨交加、天地巨变的时代,进而和时代一同成长,得着了生命的历练。
当我睁开懵懂的双眼,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世界时,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红彤彤的革命形势,耳中也充满着革命口号和战斗歌声。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也还过得去,却有一种斗争的激情在鼓舞着,因为我们的眼前都展现出一幅激动人心的宏图大业:“为解放全人类、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而奋斗”!
当巨浪退去,海边往往留下各样的贝壳。同样,在那个“火红年代”里度过了的青春,也载满了多少难忘的记忆、已过的轶事,和动人心魄的情怀。
是血肉之躯感受了一场狂风暴雨,是年轻灵魂承受起许多起伏跌宕,是社会大潮催征着生命的航船,这就是半个世纪前我们的七十年代!
桌上灯下,泛黄的黑白照片和陈旧的日记本,依然散发着那个远去年代里燃烧的激情和青春的躁动,像天边的一曲长歌,渐渐飘来,婉转悠扬,感人心魄,声声不息,也勾起了一幕幕深植心间的回忆……
回忆五十年前的芳华,像那高山峻岭,像郁江波涛,她永远不老。这是一支回荡的长歌,永在我的心头萦绕。
■作者简介
周密,
江苏人,出生广州。
1982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199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
美国喜万年集团首席财务长
■目录
感谢
前言
第一章:火红的青春
第二章:翠绿的村庄
第三章:知青屋见证
第四章:变革的前夜
第五章:踏上新征程
内容试读
火红的青春是一首高亢的歌。
上初二的一天,语文老师冯怀财对全班说,你们是中学生了,要学会写日记,养成写日记的习惯,鲁迅先生就是每天写日记的。
我很听话,回家就向父母要了一本笔记本,开始写日记。记什么呢?每天上学放学,也没什么好记的,我就把自己有感而发的东西写下来。七二年七月六日,我写了第一篇日记,就是散文〈向前的路〉,那天是我家搬到贵县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我们阔别了珠江三角洲。…
从繁华的闹市到僻镇田乡、从平静的下游到腾涛的激流,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
所以我的日记不是每天记,而是有感而发、有事才记。没想到这个习惯竟然保持了几十年,成为今天能写回忆录的主要资料。
繁华的闹市是平静的下游,“僻镇田乡”反倒是“腾涛的激流”!我七十年代的回忆录,就是在这个所谓“腾涛的激流”里的故事集。
上山下乡,便是这十年中的重头戏。在当今的汉语中,“知青”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远超“七十年代”。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去杨屋村插队,和我一起的还有同班同学罗水亮,户籍随我们一起到了那里。我们俩被安排住在芦塘知青屋的一间小屋。第二天晚上我趴在知青小屋的床上,开始写下乡后的头篇日记:
昨天,坐着一辆卡车在锣鼓声中离开城镇,来到大岭公社江兴大队第十五生产队。
昨天夜里刮了一夜大风,清晨又下了大雨,房屋里还漏雨,我们半夜起来接水。天是凉了,可是心里却越热了。
从抵达到现在,队长来过三次,和我们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给我们安置了箱架、桌架、蚊帐架、门架子,装上了竹钉,还和我们一起吃了两餐饭(给我们拿来吃的),谭祖珍和杨玉娇给我们安平了床……,晚上我们谈了很多。
23日早还在睡觉,结果“睡落枕”,早餐是谭祖珍和杨玉娇给煮的,干活的农具今已准备就绪。
一天在下大雨。中午雨稍停去打一桶水,结果问来问去都找不到井在哪里,小孩子给我指向一个水塘,一脚踩陷,直湿到卷高的裤脚。原来杨屋村的井就是一个塘啊。后来顺着正路回来了,没迷路。我认为这就是一个胜利。
今天在马灯的光下,写下了这下乡后第一篇日记。”
下乡的头一天晚上,罗水亮和我盘腿坐在新搭好的床上,在知青屋的马灯光下和老知青谭祖珍、生产队政工员杨玉娇聊天,她们正在向我们介绍杨屋村,我还记得那次谈话。
“我们是八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已经有你们四个插青了。”杨玉娇说。村里的人都叫我们“插青”,即插队青年。
“是”,谭祖珍说:“我和黄玉珍是七一年初中毕业来这里插队的,现在加上你们两个。”“不过大队成立了茶场,黄玉珍就去咗茶场。”祖珍接着说,她的声音很好听。
“茶场?”我稍微向前挪了一下,想要更清楚了解这些情况,这是我第一次和农村零距离接触。
“大队在大黄山后和古平大队间的山坡上开荒种茶,从各生产队抽民兵到那里去,还建了几间房子,他们就住在那里。”玉娇说。
“他们比我们可轻松啰,是专业户,干活穿鞋带袜!谁都想去茶场,但名额有限。”祖珍补充道,言之下意,我们干活是打赤脚的,和茶场的活没法比。确实如此,在水田劳动,一年到头基本上不能穿鞋的,时间一长,就习惯了。我带下乡的鞋袜基本都没用,除了去公社县里开会才穿一下。
“你们村才八户人家呀?”我好奇地问玉娇。
“是啊。村头第一户是大爷家,后面是二爷家,二爷已经过世了。祖屋后面是三爷家,祖屋里住着四叔、五叔、十叔和六公,还有二公家的和六叔家,一共八户。接你来的队长就是十叔。”
我和水亮听得一头雾水。
祖珍看我们迷茫的眼神,就解释说:“杨屋村是春字辈和树字辈,春字辈是阿公辈,现在只剩下六公和七公了。他们一共有七户,但三公的两个儿子树兰和树桂早就各起了房子,就是八户。”
玉娇继续补充道:“二爷树兰早就去世了,三爷树桂是大队医生,养有九个仔女,两个最大的仔都去咗当兵。十叔是六公杨春和大儿子,他们一家就住在祖屋那边,还有六叔是副队长,杨树芳,他们一家在祖屋的旁边盖了房。”
祖珍介绍玉娇:“她是政工员,是七叔杨树芬的大女儿,也在祖屋旁边盖了房子,他们家也有七个仔女呢!”
没想到就八户人家还有这么复杂的家谱关系,再介绍下去我们恐怕要彻底糊涂了,还是假以时日慢慢来吧,我就想了一个简单问题:“你们全村都姓杨吗?村里有地主富农吗?”
“地富都没有”,玉娇说:“听老辈说,我们这个村是杨玉高开始的,他是我们村的祖先,我们都是这家的后代,到春字辈是第五代,到我们是第七代了。”
“哇!”我没想到这个以为简单的问题又差一点引出一串杨家丰富的历史传承关系,幸好玉娇自己转移了话题,她瞄了一眼祖珍和水亮,对我说:“你的普通话讲得这么好,和他们都不一样。”
“他是一九一医院的。”水亮抢着说。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在贵县几年我都没学贵县话,这次来我一定要学讲你们的话,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
我曾是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在学校是班长兼团总支委,这次是坚决志愿和地方的同学们一起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才来到这里的。我深为自己只会讲普通话而感到内疚,觉得来到农村一定要好好磨练,洗掉身上所有干部子弟的味道,完全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
02
但我还真不知道会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是我在贵县能够一帆风顺、备受青睐挺重要的一个因素。
虽然出生在广州市,我是在军区大院里长大的,周围是纯粹普通话的环境,根本不接触广东人。文革中,我们的八一学校为了表现革命,接受过住在附近省委汽车大队的一些工人子弟插到各班,结果来我们班的杨银玉、陈金娥和刘启华因他们的广东话口音和长得黑,穿着有点“穷酸”的样子,很快成为班上的笑柄。他们说的话常被模仿,调皮的同学们给他们分别起了“杨卖煤”、“陈做煤”和“杜!”的外号,搞得他们在班里不敢说话,完全和我们融不到一起。
随父母下放转到贵县铁小附中上学,我就被置身于方言土语之中,当然也有几个附近冷冻厂的子弟和我们一九一医院的子弟,讲普通话的就在一起玩。高中是贵城镇的向阳高中,城镇子弟为主,他们讲贵县话,和广东话还不一样。还有农民子弟,讲他们村的话,比贵县话更“土”。但学校是规定普通话教学的,所以我不需要也不屑于去学那些土语方言。
在贵县我成了个异类,就像刘启华他们插到八一学校来一样,语言不同很难和同学们搞到一起,所以只好在学习上用心,成绩就好,一直受到老师和不少同学的青睐。高中第一学期在南山分校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廖老师要我们比赛朗诵毛主席诗词《浪淘沙·北戴河》,我们班的丘玲同学经过认真反复的练习,第一个站起来,字正腔圆、大声地朗诵着: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茫茫都不见,
知向谁边……”
她父母是老师,普通话也讲得不错,可还是不可避免带点贵县口音。等到我站起来,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朗诵,轻轻松松地就得了第一,廖老师还对我印象很好,我都有点为丘玲同学感到惋惜。到了第二学期,我就被老师任命为班长。
后来我参加玉林地区的知青积代会,八个县共六百多人参加。我在会上作了一个「扎根农村 大有作为」的发言,在地区大会上发言当然用普通话。没想到会后就收到许多来信,大都是女知青写来的,还有写诗给我的。而我只是会上十几个发言中的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受瞩目?我妈妈知道了还专门来信叮嘱我不许在农村谈恋爱。我当时不知道这原来是我的普通话起了不小作用,因为广播电台、样板戏和电影里的普通话让这些县城里的年轻人的耳目一新、向往不已,所以能讲一口纯正普通话的我就成了“凤毛麟角”。
但当时的我只是深感自己只会说普通话就是干部子弟身上的旧习气和优越感,是妨碍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障碍,我深以为耻,下决心要用艰苦的汗水把它冲洗干净。我利用一切机会向社员们学杨屋村的土话,常常在劳动中引得他们阵阵笑声,给艰苦的劳动带来不少乐趣。不久后在我们的知青屋里便出现两种语言了,罗水亮和谭祖珍讲贵县话,我讲杨屋村土话。反正这些话不是区别很大,沟通起来没有一点问题。
积极学习当地的土话成为我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途径。
后来我参加过一个工作队,县里派我们进驻客家人聚居的地方,那里讲的是客家方言。在贵县的乡下说这种方言的地方还不少。县城人看不起他们,说他们的话是“蟆拐话”,蟆拐就是蛤蟆的意思。但是我到了他们那里以后,只用了三个多月就学会了他们的“蟆拐话”,和他们自由交谈了。在工作队中,学当地话的就只有我一个,其他人都坚持自己家乡的方言。那时候记性好,学话快,我却不学贵县话,因为我觉得毛主席是要我们知识青年去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接受再教育的,又不是要接受城镇人再教育。你们这些城镇的知青,才应该学习贫下中农的语言呢!